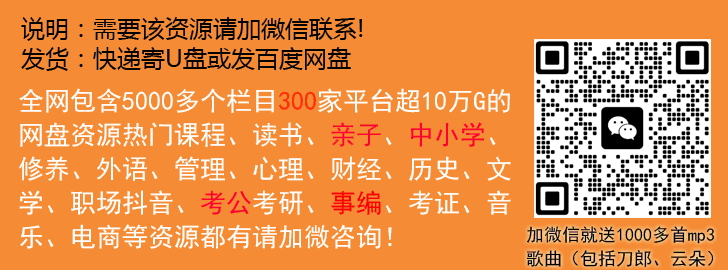星光不问前记:在《论 恶 (一):恶的现象》中,作者非常详尽地分析了恶的各种现象,信息量非常大,我看了三遍,一时还无法完全消化。恶是大多数人“不自知”的行为,恶有道德之恶、平庸之恶和欲望之恶。今天,我们往下思考——恶的机制。
文/王建平
二、恶的机制6
思考到这里,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我们尚处于社会,恶就不会消失。虽然恶表面上看是一种个人化行为,但背后的原因却是群体化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希图某一天恶人们突然良心未泯洗心革面。换言之,尽管我们向往公平正义,但每时每刻都会遇见不公平的事儿,大至利益群体对你进行思想改造,小至你随时会碰到一个不讲理的人欺骗你的人,这才是常态,而这种常态汇聚成了人类深重的苦难。人生充满苦难就是基于这个事实。
如果不在这个层面上进行思考,个人的精神修为就是闭门造车,就会割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就会遁入追求宇宙一体追求生命另外次元的虚妄认知,这种认知经不起社会检验。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一门哲学(包括宗教在内)都起源于对恶的认知,但如果不持续地直面问题,它将会成为一个“起源于智慧,发展于狂热,结束于愚蠢”的过程,更严重一点,它本身就会发展为恶。海德格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旦我们承认恶是社会中具有确定性的因素,无可避免地会产生痛苦与恐惧。这是一种普遍化的痛苦和恐惧,它也深深包含在心理问题之中。比如一个在学校受到欺凌的孩子会患上抑郁或者恐惧症。比如一个在家庭不和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会对异性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甚至排斥感。如果说女性受到性骚扰的经历普遍化到令人咋舌的程度,那么一个人被欺辱以致于留下心理阴影的现象应该比之更多(本人就无法忘记小时候被小流氓欺诈勒索的场景)。面对恶、制造恶是我们成长环境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其中就个人而言无非是量的区别而已。为了逃避这种痛苦和恐惧,人会不断地质疑自己,但这种质疑如果没有思维上的启蒙,只能制造更多的恶。一种典型的质疑就是怀疑自己,之所以痛苦与恐惧,之所以遇见不公平的事,可能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人们会想办法将恶合理化,不然觉得活不下去。比如幼时遭受诱骗的女孩,她会“自以为”自己爱上对方,不然她无法接受自己被诱骗的事实。一旦这种质疑得到观念上的承认,人们就会有意无意地惩罚自己、报复自己甚至毁灭自己。这种报复不仅体现在自身上,也体现在她周围的人身上。他们会伤害爱人,甚至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个过程,作为个人是无法察觉的,更谈不上自我启蒙、自我反思和自我精进。人长大所要经历的一切,用任何文字去表达都是苍白无力的。
从这个角度讲,心理学对一个人的心智成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学业环境的辅助。可悲的是,我们当中至今没有任何人接受过类似的教育。我们的教育缺失了“如何爱自己”这个重要的环节。或者说,我们的教育有时还充当了竞争焦虑的幕后推手,许多人的心理阴影就是在学生时代留下的。如何面对恶,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和学习的课题。7
《思想史》的作者彼德·沃森曾说,如果二十世纪的议题是科学,那么二十一世纪的议题应该趋向人的心灵。历史其实已经证明,仅靠科学不能拯救人类。相反,这个社会也许会成为《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的结合体。如今我们似乎可以闻见这股扑鼻而来的气息:网络能够让你学到很多知识,但也能够成为一批人的批斗场和另一些人的绞刑台。我们的信息暴露在网络中,这和我们的身体赤裸裸地暴露在紫外线之下没有任何区别。高铁能够缩小地域的距离,但缩小不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每个坐在高铁上的人行色匆匆,仿佛这辈子还有很多路要赶完。你有看不尽的电影和电视,不愁没有刺激的小说读物,但最终弄不清谁的生命被谁消耗在一大堆流量之中。医疗技术解决了以前不少的不治之症(同时也会冒出不少新的不治之症),但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与自杀率却不断攀升。你以为自己因为科学变得更自由,最终却发现没有一个地方可躲藏。许多孩子像吸食鸦片一样迷恋网络游戏,又像马儿一样被赶到学业的跑道上,他们的学业负担并没有变得少一些。科学能够彻底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结构,却对人的心灵无能为力。
心灵的成长是唯一解决之道。然而这条道路依旧荆棘丛生,每个人都以为这世界上定然有某种方法能够像治疗感冒一样解决自己的心灵问题,也有不少人跳出来现身说法告诉他们,只要努力,一切都能够实现。这种彻头彻尾的谎言不仅挂在心灵鸡汤者的嘴上,甚至被写进了孩子们的教材中。正如皇帝的新装,没有人愿意承认恶的普遍性,也没有人愿意放弃更多的利益。一切都在心照不宣中进行,但如果一旦有恶行发生,便觉得气短胸闷认为自己所在的是非人间,便吁长叹短叫唤着人心不古道德崩坏,便要穷尽手段将恶人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然而,这就是人世间的常态!我们要面对的恶终究是日常的恶,终究是凡人的恶,终究是社会运转中产生的观念之恶。恶从来都不仅是人性的问题、责任的问题和道德的问题。即使你拥有大智慧和大觉悟,也无法消化掉这世界所有的恶。旧的恶不断消失,新的恶不断产生。但这不意味着你无法面对恶,无法思考恶,无法在这个世界继续生存下去。你之所以在这种日常中感到恐惧和绝望,或者保持冷漠和麻木,是因为你从来只关心“我”的议题,却从来不关注“人”的议题和生命的议题。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对眼前存在的一切缺乏代入感,因为比起害怕失去一切的恐惧,我们对心灵的漠视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你知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若非经历生死磨难,就仅仅是知道而已。
你知道人最终什么都带不走,但若非在弥留之际,就仅仅是知道而已。
你知道名声、财富和权利在你死后全是虚无,不管遗臭万年还是留芳百世,和你无关。但你也就仅仅是知道而已。
你知道人最基本的安全感在于生存权,而吃饱穿暖的议题对很多人都不再是最重要的事儿,但你的安全感并没有在解决生存权后得到满足。因为生存权后还有生活权,还有社会尊严的比较,虚荣心的比较,地位的比较……你得确保自己得了重病之后有钱能够保障你继续呆在ICU里,你得确保子女拥有不输于他人的教育资源以使他在将来不落后于人……
原本我们的恐惧和痛苦会成为强烈的信号,督促我们去认真思考这世界和我们心灵之中业已发生的不对劲儿的一切,它是通往意识世界的一扇大门,但我们难以忍受这种阵痛感,拼命寻找关上这扇门的方法,以期闭目塞听获得暂时的宁静。心理学、神经科学乃至哲学,这些原本可以帮助我们珍爱自己的手段,变成了故弄玄虚的神秘知识,变成了营销者的伎俩,变成了屈服于旧有思维的催眠术,我们以为这些是帮助我们消除痛苦的魔法药物,我们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痛苦和恐惧身上,甘愿当一个委屈的受害者。
比起痛苦,我们似乎更愿意保持麻木的状态。可是,一旦我们意识到恶行原来离自己并不遥远,一切旧有的认知都会分崩离析,于是我们又急于寻找凶手,像割韭菜一样。我们以为是因为有了恶人才产生恶,殊不知恶的是这片土壤,恶人不过是土壤上一棵微不足道的苗木而已。
恶是一种行为,恶是一种认知,所有的行为和认知都指向人的思维。道德之恶、平庸之恶、欲望之恶,其真身不过是人的思维,只是这种思维已然是沉疴,如万年未洗的碗碟器皿,即使这副器皿价值连城,也已成了病菌的天堂。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状。我们只能以“恶必然存在”为前提去推动自己的思考,就算你不断地去寻找人性的良善的闪光点借此自我安慰,也改变不了这一局面。道理很简单,一道恶行对你的冲击可以抵消百种良善对你的感染。即使你身边有九十九个人在目前的情境下不会伤害你,但如果还存在未知的第一百人有可能从楼梯口窜出来捅你一刀,你的不安全感就不会因为九十九个人而降低一分。因为恶的确定性,它的杀伤力就无比强大。这种杀伤力并不体现在它爆发的时候,而在于你不确定它何时爆发,它一直会成为悬在你头上的利剑,正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一样,只要你身处异地,面对陌生人,就永远不可能确定对方是不是携带了病毒(哪怕这种可能性极低,也不妨碍你成为一个准PTSD患者)。你必须随时防御,保持紧张的状态,做好一切能做到的措施,你必须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谨慎地说话和做事以免得罪他人,但在你如此争取自己的安全时,幸福感早就消失殆尽。那时你又会问自己: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恶人只能被憎恨吗?不,有时他们还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无所顾忌,不需要像你一样到处防着陷阱,对他们来说,作恶也是一种人生方式,你在他们身上体会不到什么叫作恐惧。总结起来就是:他们很自由。最近风行的美剧《杀死伊芙》正是这种代入感的体现,角色在替我们杀人,角色在替我们自由,观剧时我们几乎不会想到自己如果是被杀的对象会怎么样,我们只是从杀虐者眼中看到了那种不羁的被解放的压抑感,他们在过我们完全过不了的生活。美国被关在牢里的变态杀人分子都可能拥有自己的铁杆粉丝,他们不断地给这些恶人写信以表达羡慕之情,这些粉丝难道也是心理变态?既是也不是。在他们的眼里,这些所谓的恶人恰恰是有着坚定的生活之道的人群,是冲破道德伪善且毫不在意世人看法的先行者,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眼里看不到愧疚,这让人疑心杀人的背后有某种“正确的”理念在支撑,而这种支撑极少体现在唯唯诺诺生活的人身上。正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枯燥乏味的经不起检验的善意让人们感到极端倦怠,正是这种所谓的道德将人们推向恶的一端,人们不会也不想思考,在他们的眼里,这种思考方式和僧侣的修行大同小异,不仅可笑而且令人疑心。他们只是希望有人能够切实地引导,能够明确地指向一个许诺之地,就像耶稣所说的天堂。8
我们必须回到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跟前:如果这世界充满恶行,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并不是某种答案,某项措施,更不是与恶相对立的对抗方式。它的出发点也绝非是如何保障我们的安全之类的指向,因为正是这个问题带来的紧缩的封闭的心理感觉导致我们产生了恐惧。这恰恰是外在的恶制造了自身之恶。这里的“我们”也并非是所谓的良善的集合体,不是相较于恶人而言的另一群体,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生命,我们和恶行的关系千丝万缕。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更深入地推进一步,就会变成:我们对待恶的态度是什么,如何去体验这种态度?
这个问题把哲学和心理学,不,应该是第一次把人的议题摆在了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模糊所有知识的边界,放弃西方式的概念化判断,才能够做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也就是说,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必须具备思辨能力,不能固执于“我”以往的生存经验,而是从一个普通生命体的角度出发,努力看清楚问题的实质。这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知识和经验不再重要(它影响了我们的思维结构,所以有时候甚至是一种阻碍),重要的是体验,体验才是新鲜的足以让人们当下就能够实现的。只有放在普遍体验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知晓事实,而这事实其实一直都很简单:生命面对各种苦难是毫无抗争之力的。很多人看到这个结论,他头脑当中的经验立刻会跳出来说,这是假的!这种本能反应是能理解的,因为此结论会立刻推翻人类固有的认知,会产生认知被颠覆后的恐惧感,所以会立刻去寻找反驳的依据。要知道,一个人如果意识到自己前期的认知不过是一场误会,就会陷入可怕的虚无当中。但是请注意,这种经验并非人生真实的阅历,而是教育洗礼(思维形成)的结果。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强调必须放弃“我”固有的经验,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也极其痛苦,因为每个社会人都是观念的受体而非创造者,不管他(她)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法国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阐述的,每个女孩在出生时都是被迫成为女孩的,是“女孩”的观念而非她的性征让她变成了女孩,而观念是从小到大被灌输的。直到她对女孩的观念习以为常,成为一种本能,她就成为社会女孩了——她具备了社会要让她具备的女孩应有的思维。其实不仅是女孩,这本是社会人的成长轨迹。而我如今要做的,就是反思并且揭露这种轨迹的可怕,对这种观念保持质疑,并用质疑推进对真实性的思考。思考的结论正是这句话:生命面对各种苦难是毫无抗争之力的。
作为个体,这种软弱无力的状态几乎每时每刻都能得到验证。从根本上他(她)反抗不了个人命运的不公平和不公正,他(她)不知道厄运何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虽然他(她)采取了各种方式保障自身的安全,不管是积累财富还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或者依附于一个利益群体,这一切不过是打造了一个虚幻的笼子,面对恶行,这一切都毫无用处。甚至我们还可以反推论:财富、美貌、权势,恰恰是恶产生的诱因。绑架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毫无意义,诱骗一个丑陋的妇人似乎不符合大部分男人的兴趣,而权势在成立之初就得不断地预防侵蚀(看看人们为此苦心制定的各项措施吧!),无权无势就缺失了腐败的基本前提。你的社会地位越“尊贵”,风险就越高。得到什么,就意味着你会失去什么。得到越多,摔得越痛。能量守恒论在这里出奇地符合我们的境遇。老庄恰恰就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对“丑”情有独钟,如《逍遥游》笔下的那棵丑树,恰恰是因为它一无所用,反而颐养天年。作为群体,显然比个人拥有更多的力量,比如在面对自然灾害方面没有群体的力量是难以想象的。但请注意,自然灾害本身和恶没有关系(相反,人类因为它而成为了利益共同体,才能造就一个个反抗灾害的奇迹,才能一次次把人类从毁灭边缘挽救回来),恶注定具有人为的社会的因素。如果非得说有关,那也是人类之恶导致了自然灾害发生。有时候,恰恰是“人祸”导致了灾害的蔓延。细究这些“人祸”,也绝不是个人的行为,有时恰恰是某一群体的“愚蠢”和“固着利益”导致了灾难。尽管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从任何角度看都缺乏一种严谨的依据,但其结论却不断被事实所佐证:群体的思考能力不足,群体是非理性的,群体接受的是情绪而非思维……任何一个聪明人只要融入群体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思考力的白痴。
所以个体和群体都没有实质上的能力去应对恶行,但它们都具备了制造恶行的各种条件。道理很简单,人类无法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无法简单地进行角色和观念的切换,无法以一己之力秉持公正和公平。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更有底气反驳我的结论。比如你会举出虽然进展缓慢,但人类文明的确在进步,例子也很多,比如种族歧视的消融,妇女地位的提升,儿童权益的保障。但请正视一点,种族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女性地位虽然相对提升,但任何一个女生都不会对此感到满意,儿童权益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他们本就是成人的保护对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是我们取得的那一点可怜的进步,其时间跨度也长到难以想象,黑人在美国的地位变化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而现在不少亚裔仍然抱怨自己在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妇女权益的历史就更长了,人类历史那么久远,但女性投票权直到上个世纪初才在部分国家得以实行,电影《妇女参政论者》很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历史,并且在片尾打出了各个国家实行妇女投票权的时间,发达如瑞士,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有了妇女投票权(讽刺的是,反对投票权的也是瑞士妇女),而沙特阿拉伯是2015年……就算是这样的变化,也是不少妇女们用鲜血换来的。表面上看,他们是为自己的权益作斗争,其实他们是在和社会观念作斗争,而这一切抗争,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都还没有画上句号。我们不是已经消灭了恶或者遏制了恶,无非是恶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如此而已!
9
生命是脆弱的,这不仅仅是身体层面,也体现在心理层面。很少有人不受他人影响,不受社会观念影响,不受传统道德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还像高中生写作文一样,认为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未来由自己创造,那就显然误会了“命运”一词。不论是制造恶,还是面对恶,前提都在于一个“我”字。这个“我”并没有体现我们独立的思考能力,却给了我们一种能够拥有什么的幻觉。我们的恐惧不在于恶行得不到遏制,或者恶行无法确保消失,而在于恶会剥夺我们的“拥有”。而恶的逻辑也和前者奇迹般地一致:你必须夺取别人的“拥有”,因为这种“拥有”是一种竞争的结果,而这种竞争从一开始就不太公正,就是强权者的游戏。正因如此,我们才不得不采用恶的方式去夺取原本属于我们的“拥有”(革命一词因此产生),你说这是一种恶行,我认为现实就是如此。如果现实就是恶,那我只能遵从这种恶的指令,否则我就一无所有。与其一无所有,不如就做个恶人。为正义而恶,能叫恶吗?
出于同一个理由和同一种逻辑,我们开始了恶的攻防战。没有人抽身而出,看一看前提是否有误。也许你会说,战争开始时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还有谁在意战争的理由?但又是谁给你贴上了“士兵”的标签?难道不是你自己吗?事实上,那些动不动就用战争形容人生的人往往是没有真正经历过战场的人。比如那位说“有奥斯维辛,就不能有上帝存在”的作家普里莫·莱维就不可能轻易将人生比喻成集中营,因为他知道集中营的可怕。我们缺失了“人”的视角,才是把人生的得失当成一切的最根本原因。因为这一视角的缺失,我们才对生命本身缺乏代入感。我们把自身的社会属性和拥有的社会观念当成了“我”的全部,漠视了生命的议题,同时以一种很不严肃的态度对待超验的部分。对他们来说,这部分内容只能交给宗教去解决,教给信仰去解决,甚至教给灵修者和心理医生去解决。今天能赚多少钱,今天能收获多少快乐,今天有多少人来爱我,这才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恰恰给恶行的产生提供了无比肥沃的土壤。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佛教“无我”的概念,自然也不可能完全践行灵修者和宇宙本是一体的理论,但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下自己:你了解人本身吗?如果思维是一张全景图,而我们的“我”则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孤岛,站在孤岛上就以为自己掌控了人生,这算不算一种无知?
当我们在探讨恶这一话题时,首先检验的应该是自己的视角。之所以仅仅只有“我”这样一个视角,并非人类生而有之,这是社会思维发展的结果。《知觉现象学》的作者莫里斯·梅洛-庞蒂(他同时也是一名心理学家)和萨特、尼采等人不同,他注重于将哲学观念应用于生活(这恰恰是心理学的使命)。他认为,经验是肉身和意识不断交叉汇聚的过程,在关注儿童心理后,他意识到知觉是一种从学习到本能的过程。这种学习不仅体现在知觉上,也体现在经验积累上。但出于对现象学感兴趣的缘故,梅洛-庞蒂对后者的描述较少,其实我们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我们所谓的“我”,完全是被动学习的过程,是一种经社会浸染后所产生的认知。
我们知道,一个被截肢的人会产生“幻肢”的错觉。一个人可以去寻找身边的烟灰缸但从来不会去考虑自己的手现在放哪儿了,这就是学习最终化为经验本能的结果(哪怕你能够寻找出其神经运作的机制证明“幻肢”和社会认知没有关系,也无法了解神经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但请注意,经验本能不仅仅是让你察觉到手的存在(哪怕它已经被截肢了),也会让你察觉到“我”作为意识的存在。这个“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概念化,以至于我们确信自我意识的存在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相反,失去自我等于否决了一切,因为所有的价值感都依附在自我身上。这个过程是谁都摆脱不了的。佛学恰恰是看到了这个现象(哪怕它没有遵循现代心理学的轨迹),并且认定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我”身上,所以才提出“无我”,你想想看,连“我”都不存在了,那么这个体验恶的人是谁?但这个概念吓走了一大半人,没有人愿意舍弃旧有的经验,这种经验带来的价值感一旦失去会造成巨大的空洞,那种感觉和拔掉一颗驻牙后产生的不适以及戒烟者觉得自己某样东西被剥夺是一样的,甚至程度更深一些。大部分人都不可能舍弃旧有的认知,哪怕它从来没给自己带来一丝快乐的感觉。但我想提醒那些专注于佛学的人,“无我”一旦变成了追求,也会成为某种固有的概念,一旦如此,它和“我”也不存在什么区别。问题并非仅仅在“舍弃”上,恶也并非仅仅出在个体化的“我”身上,而是出于社会思维上,因为有无数个“我”的意识,才制造了恶。靠个人修行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否则宗教和哲学早就拯救了世界。思维不是孤岛,它是有别于互联网的另一张网络,它也能下载,也能浏览,也会存在病毒,每个人的意识都是网络上的节点,如果这张网在整体的运行方式上出了问题,个体永远无法幸免。如果和整体的网络有冲突,它就会被排斥,种种的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仅仅源于童年源于力比多,也不仅仅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调和作用,而是这种冲突的结果。把人作为孤立的现象去研究,心理学就会在“社会神经症”现象面前失语。而这种现象所造就的恶,我们在微博上就足以窥其全貌。从这个角度看,抑郁症和焦虑症根本不是神经症,反而是心理冲突外露的迹象,正如发烧是体内白细胞与病菌抗争的结果,相反,自以为是的判断,对不同言论的敏感,集体激情的幻觉,这些才是真正的神经症。只是一旦大多数人具备了这个特征,没病的就变成了有病,有病的就变成了健康。这正如如果大多数人发疯,那疯人院就是为正常人所设的。
这个发现对我们的思维存在多大的意义?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很确信:无论何种恶行,都不是个人化的结果。这是一种思维的精进和拓展。举一个最能挑动人们神经的例子:如老师猥亵女学生(媒体对这个话题总是最热衷的)。如果没有思维的精进,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个人化的恶行。这样想是因为问题容易解决,只要把这个老师关进大牢就万事大吉了。再有人稍稍加以思考,就会提出另一个疑问:为什么这种品行不端(你看,又和道德联系在一起了,因为缺乏思维时,道德就是一切的答案)的人能够混入教师队伍?这个问题虽然比前面的有难度,但似乎也可以在教师准入制度上加以完善。不过,这个答案把一切的恶都归入了反道德的范畴,过于简单化。如果道德能解决一切问题,世界不会以现在这副模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糟糕的是,每个国家的道德概念也不尽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但如果我们抛弃“我”的所有观念,用思维的全景图去思考,就会提出更为本质而简单的问题:是什么思维和观念导致这个人竟然猥亵自己的学生?又是什么观念导致了这位女学生被猥亵而不敢反抗?
当你去细究一个人为什么会产生犯罪的举动,问题就会变得复杂。人作为群体最讨厌的恰恰就是复杂。但只要我们继续观察就会发现,没有一种现象是孤立发生的。现象学家胡赛尔认为,我们应该如实地观察现象,对内在的经验及情感因素进行悬置判断。所谓的“如实”其实也难有具体的标准,但至少能够明晰一点:不要在观察时渗入任何道德的判断。这个观点和我们东方哲学似乎不谋而合,但我们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作“因缘”。所谓因缘,就是万事发生皆有因,现象不过是一种果而已。我们如果不去注重因只看结果,思维定然是固化的片面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果同时也是一种因,会导致其它现象产生。比如老师猥亵学生这件事并不孤立,它还会产生其他的现象,比如这个女生接下来的生活必然受此影响,当然这位老师也是。因此,现象是思维的具象化,就像意识海洋里的波浪,一浪推着一浪走,彼此相关联。我们可以沿着某个现象追溯,会发生它是由无数个其它现象推动造就的,因此恶的产生必有其因,而且不止一个。恶的背后有无数的推手,那是靠法律和道德无法解决的。
这种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恰恰是我们缺失的。如果我们除了在法律上惩罚恶,在道德行为上排斥恶,还能更进一步,去细究恶的成因,就能阻止下一个恶的发生。但我们的社会运转方式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目光停留在结果上,而且总是有不乏吸引眼球的结果供我们讨论,谁会在意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而这恰恰是最大的恶!
依然用老师猥亵学生的例子,我们如果追溯这个老师过去的经历,会发现他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他,是无数人和事影响的结果,是观念和行为塑造了这样一个可悲又可恶的人。问题在于,我们会发现塑造他的方式不仅不可逆,而且似乎有其必然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经历过某些事件和观念的洗礼后,他作恶几乎是一种必然。为什么?因为他同样缺乏思辨性的思维。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这种恶人的产生,在平时和其他人的接触上,通过大街上父母的语气和孩子的态度,也似乎能够嗅到他的成长轨迹。虽然这种轨迹无法精确确定,但我们至少能够得知恶是一种泛化的结果,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事件。
作者简介:王建平,一个普通写作者,著有《请珍爱这样的自己》、《众生之死》等作品,心理学随笔《超限思维》已出版上市。个人微博:http://weibo.com/wasu/
王建平文章专辑:
- 论 恶 (一):恶的现象
- 观《82年生的金智英》或致女同胞
- 悉达多与肖申克——以及思想心理学的起源
- 我们该如何脱离苦海
- 孩子是神给我的
- 蠢货是怎样炼成的
- 假如注定苦难 我仍愿意幽你一默
全网知识馆hupandaxue.cn,星光不问赶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