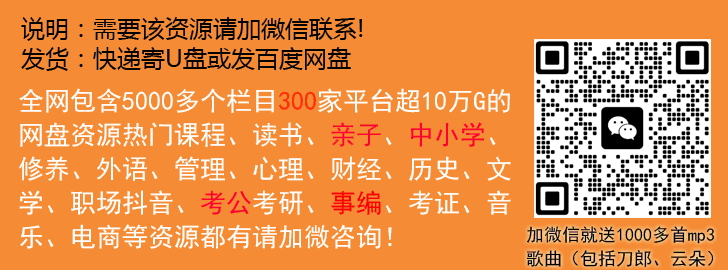文/乐不思蜀黍
一
旧城无新事,人们的消磨时光,就是和自己打谜语。
旧城的旧,和楼墙瓦砾的斑驳无关,也不是街头巷尾的幽幽荒草,它是嵌入骨子里的灰色记忆。整座城市的人、马、车都陷进去,深深地抹下阴影,扣在腰间,栓在脚上。
离峣城,妥当而贴切。城北一行高耸交叠的山把本就禁闭的通道封死,南面一望无际的大海浩浩荡荡,从始至今也没见取经的帆船由天际驶来。那时国家为了扩大版图,派遣一列四千左右的队伍向南勘察,翻过崇山峻岭安营扎寨,但再也没能翻回去。人们太累了,累的用尽了全部的补给品,而探险家骨子里的自由勇敢也被磨灭。这里物资匮乏,这列人利用自己的才智搭房建屋,发挥想象制造出一切用于日常生活的物品,也时刻等待着国家的召唤,这一年,是1910年。
起初的日子平淡而满怀憧憬,从山那头延留的习惯总是难以消磨。内陆人以杂粮为生,干旱的地理环境把再俊的伙子都打磨的皮糙肉厚,他们自诩为斯巴达的后世,也尽是版图扩张的产物。但那是30世纪前的事情了,后来马其顿的崛起也把一片天地搅得翻覆。内陆南境的崎岖不可多数,往北就不一样了,广阔无垠的大平原,稍有起伏的丘陵,一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在这片土地孕育。人们习惯也适应了与生俱来的地理优势,每日耕作,劳务,不亦乐乎,也完全不像斯巴达的血统。
和如今的州县市不同,那时的区域划定并不明确,以山为区,以水为界。内陆无山,水源也屈指可数,划分界定的任务久而久之便荒废了,人们都习惯把山南未开荒的一切称为南城,而内陆的浩大则叫作北国,合起来拼成一个国家。但莫名其妙,这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婚姻破裂且主动提出离婚者将被派遣调至南城,终身不许回头。人们是这么推敲的,既能通过远行排解心中的苦闷,也避免了每日抬头碰见旧爱的尴尬,更是重获自由与新生。当然这些只是说辞,南城的荒废和不可预测可想而知。这是离峣建立前的规定,这也真是条莫名其妙的规定,之前的人去哪了尽然不知,他们是否真去了南城也不得知晓,可离峣只有一个。
离峣真不一样,它真是勘探造国的产物。北国突发奇想决定不让南城在一堆毫无管制的离人手里荒废,而这列浩荡四千的队伍多是思乡的种儿,却也背负着南城人同等的待遇。国家可别忘了这列队伍的初衷,更别把他们当成斯巴达底下的奴隶,不管不顾。
二
环顾1910年的离峣,海风吹拂下的眼前全然却是凄凉。山脚与海岸线间不到半天的徒步抵达,几棵说不上名的树木横七竖八立着,几块巨石也参差不齐地堆积聚拢,千万年的海龟耸拉着脑袋趴在岸边,不知死活。左右望去倒是开阔,冗长的海岸线绵绵伸向两端,没有部族,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真是开荒来着。队列里有人携带着先辈流传的手册,开卷写道:南城变幻莫测,随心转,随意摇,一人一小城,一城一世界。再往后翻,又详细记录了各人的具体事例:起初悲苦交戚,味如嚼蜡,迷迷糊糊大抵两月,渐由悲转恨,掏心底,挖心窝,寥寥数月,浑然不知旧事,可谓新生。或者写着,淡然挥袖,只道枉此前生,欣喜抛却杂陈,另觅佳境。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让探险家们左右为难,该喜该悲,面面相觑,谁也不懂。
渐渐地,背后的山麓愈发黯淡,呆滞的目光望向不远处光秃秃的山顶,从早到晚,坐着站着,完全成了填满饥饿的生活习惯。有人真想往回走了,可这苍惶穹顶简直就是一面紧扣锁链的大门,任其翻爬滚打,终究连门面都没摸着。来时所向披靡的通途,如今竟毫无手策,真是座匪夷所思的山麓。
既然这样,我们就好好活下去,活是为了再次投入北国的怀抱,更是别让自己在浑噩如淖的日子里肝肠寸断。勘探造国的初衷已在无形中消乏磨灭,取而代之的这股新力量咬在齿间,抿在唇间。
山脚的碎石和杂木参差罗立着,队列里的石匠和伐木工这时便有了活计。他们拎上手里的锤子斧子,看准量好了心中确认的位置,猛一声劈下去,硬邦邦地凿下去,噼里啪啦霎眼电光火石。孔武有力的汉子从海边挑来润稠的湿泥,和上细碎的石砾,在背风靠山的阴凉处堆出四面稳扎厚实的泥墙。这时把原先钉构好的长木板铺成房顶,挑一处圆木架成房梁,拼拼凑凑一面木门掩着空出的泥墙口,一座简单的土屋就这样大体落成了。一传十,十传百,吆喝的口号喊起来,挥力洒汗,陆陆续续更多的土屋筑建起来,方方正正,排列的紧凑而工整。在没有砖瓦修葺的原始境地里,大脑便成了开发一切的源泉。
三
解决了遮风避雨的问题,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鱼虾簇生的海底。捕捞捉抓,一顿毫不利索的忙活总算逮着了几条被潮汐拍到岸边的小鱼。可内陆的饮食习惯让新大陆的人们好不适应,咸渴的海水更是虚脱了人们的脾胃,短暂的热火朝天后,一股夹着恨意的愤怒黯然升起在探险家们的心中。
马是这座国家的灵魂,倚马伴天涯,策马挥沙场,人们由生至死都和马有着莫大的关系。当年铮铮铁骑浩浩荡荡地踏平这片领土,马与人同生,但人即使饿死,也不能杀了眼前这匹马。它是宣告国家的标志,决不是牲畜。
可这一刻,有人竟打起了马的主意。朔朔棕铜般的鬃毛,健硕强劲的身躯,冷峻高贵的目光,眼前这几尊随行的马匹倒无时无刻不享受着神灵的待遇。落难离峣的人们每日四处采集最鲜嫩的青草,毕恭毕敬地安放在它们面前,待它们进食完毕才摸着逐渐干瘪的肚皮,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顿没了后顿。几个难耐的小伙子最先神色诡异地围着马匹溜达,时不时却和同伴凑近了耳语几句。不到三天时间其中一匹马却莫名消失了,而人堆里的那几个小伙子竟也跟着没了行踪,真是撞了鬼。陆续地,又一匹马,又几个人,无故失踪。再然后,队伍里辈分较高的前辈也毫无征兆地和一匹马蓦地无声,完全没了着落。
终于,留下的队伍中有人再不愿偷偷摸摸了。他径直捡起一把磨的锋利的砍柴刀,大喝一声冲向毫无征兆的马群,“猛”一狠心甩起利刀当头一劈,“噗”!!红色!鲜红的血液顿时喷涌如泉!伴随着声嘶力竭的马鸣声,整个天地顿时肃静了。海面一片红,头顶一片红,脚下一片红,万事万物浸透在粘稠冷寂的惨红里,探险家们直愣愣地怔在了原地,惊愕的表情衬在每张红红如血的脸上,僵硬凝固无法动弹。整幅画面像张薄脆通透的锡箔纸,轻,飘,柔,一团昏红的小火从底下揾揾而起,终于,“咔哧”一声,从滚烫的烧的灼热的最中央,这张锡箔纸,悄无声息、轰轰烈烈地碎了。碎了,是彻底的流于死灰,沿着中央漫漫伸向整张枯萎的边沿,又像是一面不愿再照它于心的镜子,永远的,碎如残阳,红如鲜血。
把信仰击碎的人们,终究会成为前生可畏的新生物。这时像人群里的一颗炸弹爆裂,探险家们顿时沸腾起来。抄起脚边的砍柴刀,冲向再无生息的马群,“猛”一果断甩起利刀当头一劈,“噗”!!每张神采奕奕的表情咧开了花。饮马血,吃马肉,终于没了饥肠辘辘的束缚,人们大开手脚,大吃大喝,这群落难的人们,终于成了自己的信仰。
四
食物毕竟是生存恒久的第一问题。在数星期的痛快豪饮后,探险家们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鱼虾簇生的海底。但这时候人们的心态早已不一样了,大概万事万物总会变化,倏忽间你无法知晓下一刻的转折,而你无论如何,保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连信仰都能改变的人,一点小的饮食习惯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前人罗列的情境,或许形似或许影似,终究心不似。
就这样,离峣城在不紧不慢的岁月里逐渐展开了新的生活。偶尔从广阔无垠的大海际处驶来一两艘避风遮雨的船舶,也中和在天色惨淡的黄昏里,无可奈何的清晨里,夹着寒风,浸着暖阳,缓缓地消失天际。离峣不解风情,也在后知后觉的渺无人烟里成了孤岛。
五
年复年,月复月,新城总有归属旧城的那天。这时候离峣城俨然成了一幅规矩整齐、排列有序的新模样,后辈们遗传了先代骨子里的坚韧探索精神,将这片原本简单的城邦打造地更富生机。但一座孤岛的使命,在安稳生活后,茶间饭后的谈资,却无处找寻,唯有和自己打趣,或者对着渺茫的大海仰天长啸,听那句被海水淹没的回声。附在印象里的灰色记忆,那段艰难如淖的岁月,从始至今依旧像个无法摆脱的鬼灵,在悄无声息的黑夜里钻进你的梦。不忍说,不可说,不必说。
北国终究再无联系,那些信誓旦旦的不过虚妄,而离峣,在红如鲜血的朝升夕落里,此起彼伏,富贵长安……

星光不问记:去一个地方,要融入那里,包括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惯和身体里的信仰,当很多东西已经格格不入,是守旧还是革新,是重建还是出逃,一半是火一半是水,尽管一切都没那么容易,但生活总会逼迫人们做出选择,也许到最终,想让荒芜变成繁荣,孤独变得安宁,却还得靠自己的创造。
全网知识馆hupandaxue.cn,星光不问赶路人!